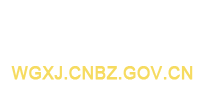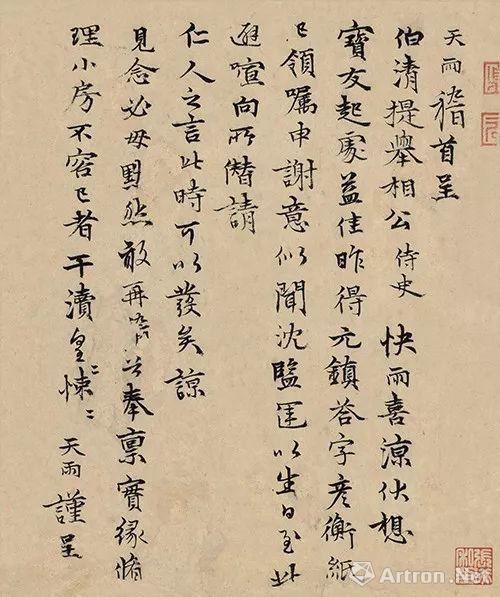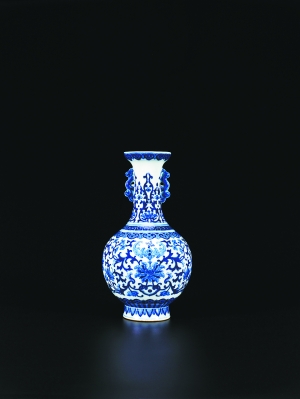道光二十三年户部银库亏空案
韩 祥
道光二十三年春(1843),京师户部银库爆发了清代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库银亏空案,亏空额高达925万两。不过,因发生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,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多被置于鸦片战争的阴影之下,而变得湮没无闻。
追查焦点:渎职 侵蚀 盗窃
在清代,户部是主管全国财政的最高行政机关,户部银库则在相当程度上扮演着国库的角色,每年超过全国财政1/4的各类地方款项被汇解至该库,由中央政府直接支配。可见,户部银库的收支直接关系着清代财政的全局。
虽然户部银库在调节国家财政上起着关键作用,且设有专司及管库大臣、查库御史进行制度化管理,但因吏治腐败、贪渎之风盛行,库银自乾隆后期便极少清理,库吏侵蠹成性。当弊政累积至承受极限时,便会以偶发小事件的形式突然爆发,道光“二十三年,库吏分银不均,内自攻讦,其事不能复蔽,达于天庭”。
这起大案是在一件库丁舞弊举报案中被揭露的。根据该年三月十八日潘世恩等人关于案情审理报告的长篇奏折,可以大体了解此案发生的过程及当时户部银库的管理状况。案件情节概括如下:
户部银库库丁张诚保之兄张亨智,想为其二儿子张利鸿报捐知州,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,托付其姐夫周二将银11474两分装11个口袋送至户部报捐。当日,由于前来报捐的监生众多,直至傍晚才轮到张利鸿捐银交库,周二令帮手张五将银袋携进银库门内,库内每称量一袋,张五即续携一袋进库。仓促之际,库丁张诚保将第2袋误报为第3袋,而查库御史与库官均没有听出其中的错误,张诚保便更大胆地在报第7袋时捏报为第10袋。这样,等到将张利鸿需缴纳的捐银称量完毕,共偷漏出银4袋(4100多两)。
之后,张五将偷漏的银两趁乱携出库外,与周二准备将漏银运走。而这种舞弊把戏被其他库丁看得一清二楚,并在库外路边谈论此事,恰好被多名路人听到。路人有意敲诈,便一哄而上拦住周二,争相抢夺,各抢得银两若干。最后剩下3700两运回由张亨智开办的万泰银号内。事后,相关知情的库丁均分得了好处,而万泰银号的几位管事人却未得好处,遂向张亨智讨要,反被辱骂,这几个人在一怒之下将其告到了衙门。最后,经该城衙门咨送刑部,弊案曝光。
此案在道光二十二年底便上报刑部,但到次年二月仍未审理清楚,户部只是重新拟定了银库收放章程八条。三月十八日潘世恩等人的长篇奏报出炉后,道光帝才得悉弊案全貌与事态的严重性,认为“此等积惯舞弊之人,恐盗用已不止此一次”“钦派大臣将库项全数盘查”“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刑审讯”。然而,案件的清查结果让道光帝更为震惊,所牵涉的京官、大员之多亦为清史罕见。
需要指出的是,此次清查户部银库亏空是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背景下进行的。当时,在广东与英国交涉的伊里布还未筹足对英的第2期赔款(210万两),加上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黄河决于河南祥符、次年八月再决于江苏桃园,朝廷急需调拨河工、灾赈的巨额银两。
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,刑部尚书惟勤等奏报了户部银库亏款的实际情况:实应存银约1218.2万两,而统计存贮各项实存银两约292.9万两,实际亏银约925.3万两。面对巨额的亏空数字,道光帝愤恨交加,认为“实属从来未有之事!览奏曷胜忿恨!以国家正项钱粮,胆敢通同作弊,任意攫取,似此丧心昧良,行同偝国盗贼”。因此, “渎职、侵蚀、盗窃”成为此案追查的焦点。
在审查中,户部银库的大量陋规被曝光,不仅库丁盗窃,而且管库大臣与查库御史都收受银库规银。
亏空追缴:严惩 罚赔 甚微
面对国库严重空虚,道光帝对此案的处理,与前相比极为严厉,几乎严惩了所有涉案官员,包括历任银库司员、查库御史、管库王大臣、查库王大臣等。于是,一场清代历史上最大的库银罚赔、追缴运动开始了。
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七日,道光帝下旨:嘉庆五年(1800)至道光二十三年(1843)间历任库官、查库御史各按在任年月,按月罚赔银1200两,已故者照数减半;其历任管库之王大臣每月罚赔银500两,查库王大臣每次罚赔银6000两,已故各员按数减半。因涉案人数众多,一时难以全部停职查办,不得不以“革职留任”的方式,让戴罪之人来查“罪”。
既定方针确定以后,大规模的罚赔、追缴便开展起来。道光帝亲自规定了处罚的等级与期限,对于涉案官员交纳罚赔银两的程序与管理亦有明确规定:应交罚赔银两每次先在户部呈报,由部移交管库大臣率库官平兑,验收后给与实收知照,户部备案,再入库另款存贮,每月随月折具奏一次,等积有成数时,奏归正项。兑收日期,以每月逢十兑收,如遇小建(农历小月)于二十九日兑收。对官员的罚银一般以在任时间长短而定,虽然谕旨中规定每在任一月罚银1200两,但在实际的追缴中则多通融为1000两。
通过对现存相关档案的统计可知,除去重复统计后,在1800年至1843年间共有321位官员(包括现任、卸任、已故)涉及此案。查证相关档案可知,罚赔、追缴运动由道光二十三年四月持续至道光二十九年六月,共收银约150.5万两,均奏明归入正项,但远少于预定的罚赔银数。
此外,清政府还采取了其他方式弥补此次户部银库的亏空,如追缴库丁、书吏所侵蚀的库银,减平发放各项开支银两,没收各省关“库吏规费”等陋规收入弥补库亏,增加征收入库岁银的附加费等四项举措。然而,这些临时举措或收效甚微、或无法持续,最后的弥亏作用大打折扣。经测算,四项措施最多能够筹得弥亏银213.5万两。
由于相关档案的缺失,该亏空追缴运动的整体面貌已无法完全弄清,但通过以上的推算可知,此次追缴对库亏银的弥补最多为363.8万两。而这对于925万两的亏空总额来说,是远远不够的。
社会影响:支出 救灾 瓦解
鸦片战争后,清政府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,对国家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。相关论著一般将战争视为造成当时财政困难的最主要因素。然而,这种观点却使我们的视线过分集中于外来影响上,而忽视了当时国内体制积弊的影响。
此案处于鸦片战争后的敏感时期,进而与战争的影响结合在一起,共同加剧了道咸时期的社会经济危机。然而,由于户部银库亏空的积累、发生与鸦片战争并无关系,所以二者所产生的影响有必要区别分析。
首先,此案影响了当时社会公共工程支出。该案被揭后,清廷立即减少了各类财政支出。道光帝紧急下发的节银谕旨要求“所有大小工程及支领款项,遇有可裁可减者即行裁减,可节省者即行节省,总期实力撙节,积少成多”。
其次,该案对当时清政府的防灾、救灾工作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。库亏案爆发前,黄河连续决口,先后波及50多个州县,清政府在战时仍从各库拨出了2000多万两巨款救灾。但在库亏案被揭之后,政府的赈灾支出则出现了大幅削减,这不仅是现实上的战争影响,更是统治者在心理上对隐性亏空的恐惧。
第三,此案加速了清代传统财政体制的瓦解。鸦片战争后,各地方省库拖欠部款的情形明显加重,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沿海省份过度担负对英赔款,以致不能年清年款。该案发生以后,地方省库拖欠户部解银的现象大为增加,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,“拖欠解银”已成为常态,从而使清代沿用200多年的“奏销制度”趋于崩溃。在这个层面上讲,此案与鸦片战争一起加速了清代传统财政体制的瓦解,形成了空前的“道咸变局”。
作者简介
韩祥,1986年生,河北安平人,史学博士,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讲师。